有人問李乃文,為了《我們的日子》里王憲平這個角色,做了什么準備?李乃文笑,我都準備了40多年,還不夠嗎?
算起來,李乃文的確是在那個時代成長。他是天津人,在寧夏出生,吃百家飯長大,就跟劇里的王雪花一樣。
李乃文覺得自己很幸運,也很幸福。從中戲畢業以后,他不斷在演戲,從話劇舞臺到電影電視劇,涉及各種題材和角色類型。翻閱他的作品,數量令人驚嘆。不僅有數量,從最開始,他演的角色就總能令人記住,演技穩定踏實,完成任務的同時,保有自己的特色。
前段時間的年代劇《我們的日子》一開播,他演的王憲平在妻子劉淑霞產房門口喊著用炸碉堡的心態生孩子,上了熱搜,這一下,軍人王憲平的人物就立住了。沒多久之前,他在《回來的女兒》中飾演90年代暴發戶王重江又心機深沉。兩年前,他在張藝謀電影《懸崖之上》演的魯明則是高級特務……可以說,李乃文留下的角色比他自己人氣要更高。
如此“勞模”,他也不覺得疲憊。他在轉場間隙接受記者的電話采訪,到了拍戲現場,還會頗有興致地拍張照片發到采訪對話框,介紹說,“這是我們拍戲時用的火車”。連軸轉累不累的問題他壓根沒想過,在他的印象里,從第一天正式進入了中戲,他就覺得自己“如魚得水,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天地”,所以,“做喜歡的事永遠不會覺得累,就像玩就不會覺得累,因為喜歡。”
真實的質感
李乃文在不同戲里的追求不同,對于《我們的日子》這部戲,“特別真實”就是他感受到的,和他必須呈現出來的特質。
“王憲平真實到你會覺得他就是你,我能想象得到他的真實存在。我之前問過我們的編劇老師娟子,你寫的這個人是你爸嗎?她說差不多,李小冉也說跟她爸特別像。”為了呈現出真實感,王憲平的衣服都是造型老師從家里親戚壓箱底的衣服里翻出來的,現在做不出那樣的質感。
一走進現場,看到那些破立柜、折疊桌子,包括咯吱咯吱響的門和床,五顏六色的大棉被,李乃文一下就穿越回那個時代。他和李小冉有時候就穿著破秋褲在現場溜達來溜達去,也不顧及形象了,真的像在家里,也真的就像過日子一樣演戲,有時候拍完床上聊天的戲,他們就干脆不下床了,接著靠在床頭聊天,“小冉開玩笑說我是她這輩子里面見過穿秋褲最多的男人。”
這點滴細節自然流露帶來的真實感讓年代戲具有質感。“我們的大部分劇照都是拿膠卷拍的。膠卷相機真的是不可控,拍一張是一張,全都留在膠卷里了,過曝了,光太多了等等,但這就是真實嘛。”
李乃文強調,環境、服化道是現場功夫,但他更看重這個劇本的真實感,因為這個故事里充滿“偏見”。
“這戲里其實沒有壞人,我們真實的生活里,壞人也不多,但是在劇中,我認為楊大山就是壞人,只是觀眾看到的楊大山絕不是壞人,這也叫真實,因為我們生活中會有很多偏見,有各種主觀的判斷,會產生一些誤會。所以,我們總是只看到生活的一面而已,但是生活是有很多面的。”
當然,這個真實的偏見也折射在主角身上。王憲平是一個暴脾氣的軍人,愛發火,他的特點很明顯,也有那個時代最普遍的北方男性身上的大男子主義。這個人物有趣之處和最大難點也在于此,“在情商這么低的情況下,怎么才能讓像劉淑霞這樣的人愛他?其實有時候劉淑霞是接受不了他的。”李乃文只能盡量抓住王憲平脆弱的時候去展現他的愛,人物被偏見和偏愛一步步豐富起來。
“他就是這么討厭,所以他很真實”
演年代劇要追求真實,就無法避開時代局限性。王憲平是一個在當下并不討好年輕觀眾的人物,他身上的大男子主義現在是會被全面批評的性格。李乃文分析說:“這是那一輩男性的共性,是時代的產物,咱也不能說是毛病,他的溝通方式,考慮問題的角度,都不是特別合適。對女性來講,你為什么不好好說話?你為什么不換位思考?但他只會用一個特別直接的方式去表達,很多時候本來是好心,結果辦了壞事。其實北方人大部分都是直男,現在比那個時代要好很多,但是依然存在。我覺得女性考慮問題的角度或者深度都比男性要好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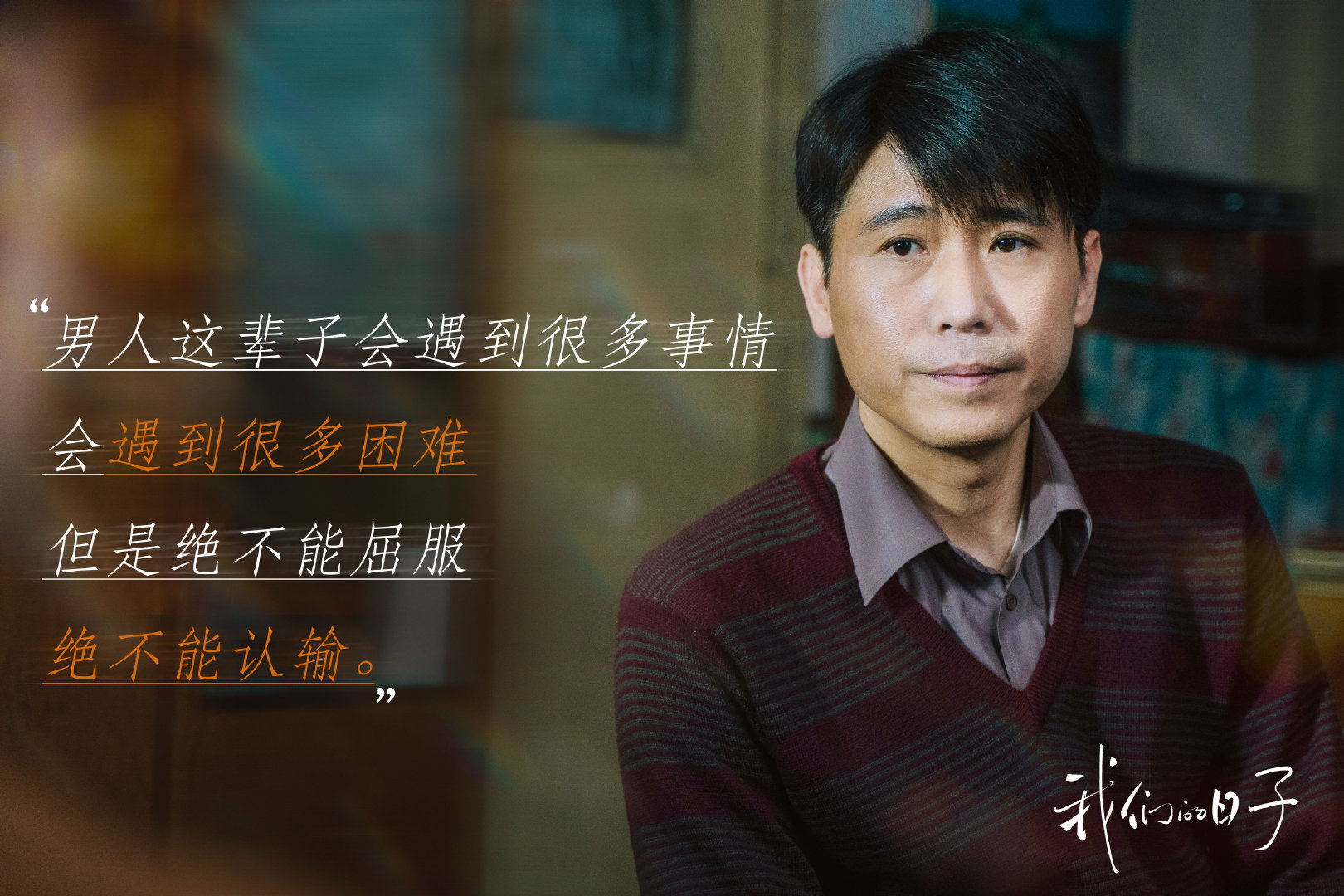
《我們的日子》臺詞宣傳照
即便人物因此顯得不討喜,他也不認為要把這個弱點拿掉,正是因為這點大男子主義,才是真實的時代局限性。
“我也看過一些評論,說王憲平太討厭了。但是我想說,對,他就是這么討厭,所以他很真實,戲里邊沒有偉人,沒有圣人,只有人。劇本就是這么寫的,我接受他,我也尊重他,我也尊重編劇,尊重這種人的存在。”
他去豆瓣,也看彈幕,看到無數人因此說棄劇,或者批評這種性格過時陳舊,給出負面評價。他不太在意演的角色能不能討好到觀眾,“人物本身就是這樣的,劇里沒有去評價這是好是壞,不去展現對錯或好壞。說實話我不會在意(那些評論),因為我是服務于這個角色,而我就是想讓這個角色不完美。”
有時候他特意去豆瓣看看差評,甚至琢磨評論者的心態。
“我年輕的時候喜歡看好評,但好評往往不太真實,但反而不好的或者是吹毛求疵的評價,一是能夠真實的反映出來作品到底是好還是不好,同時也能看出對方的心態,他不想面對真實的‘瑕疵’,但我敢。這個東西能回避嗎?如果你想進步的話,就什么都別回避。”
他看的差評不只有說大男子主義的,還有人評論,生孩子難產,老大又出健康問題,這個劇讓人恐婚恐育。李乃文的心態倒挺有趣,不僅不生氣,還能慢悠悠地回懟。
“如果覺得這個戲就讓你恐懼了的話,可能心智還需要再磨練,還是不夠成熟,看個電視劇都能嚇成這樣,生活當中會有更多東西讓你接受不了,但是你還依然要去面對,所以我也挺替他們難過的。每個人都要去面對明天的日子,誰都不知道明天會給你什么。”
“有的人還說太狗血了,但那時候我們演話劇,最經常說的話就是生活永遠比電視劇還精彩,生活永遠給人很多驚喜,可能是真的驚喜,也可能是帶引號的‘驚喜’,但是我們都要去面對。”
“有的時候回頭,停下來回頭看看,感受一下”
年代劇的錯位很有意思,我們總能在足夠接近真實的年代劇里看到王憲平這樣,當下會被負評的人物,但同時,年代劇也是不少年輕人反復在刷的國產劇。
李乃文覺得,那是因為人的本質不會變,“那個年代的善良和現在的善良,具體體現可能不一樣,但是根是一樣的。”
“當我們體會不到那個年代的人的時候,你看一眼,就知道純粹的情感是什么樣,不要匆匆忙忙總是看明天我要掙多少錢,有的時候回頭,停下來回頭看看,感受一下。昨天我還想,把30多年前看的小說,路遙、王小波的作品,都拿出來再看看,通過作品或者通過書籍,體會一下那個時代,對于我們來講不是壞事,可能會讓我們更明白該如何去面對自己的明天或者是今天。為什么年代戲還是有挺多人看,說明想要回頭看一看的人還挺多。”
回到王憲平身上,李乃文在演之前就想明白,他的目標首先是讓觀眾能對號入座,不管優點缺點,先足夠真實到像看到了自己的父親、哥哥的樣子,給觀眾一種熟悉的感動。其次,在錯位的時代里,回頭看看自己的長輩。
“我身邊的朋友有天跟我碰上以后,說看完這個戲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摟著自己的媽媽說我愛你。那么這個戲的價值自然就呈現出來了。回憶是一方面,回味可能是更貼切的一個詞,回味是指對當下自己關系的和解,跟自己和解,跟家人和解,跟自己的生活和解。”
實際上現在年代劇逐漸式微,李乃文覺得盡管自己思考諸多,但不得不承認,做出好的年代劇非常困難,“很多細節的還原度是要非常高的,包括服裝道具、臺詞、那個年代人的情感、大家善良的本性……看你怎么去體現,讓觀眾能夠接受,這個是最重要的。那個年代能寫的事情太多了,但是很多東西我們又很難表現,在有限的創作框架里,要展現那個時代的洪流,大背景,又要把屬于個體的故事體現出來,這就很難了,那就只能挖掘生活中的點點滴滴,真的很不容易。”
演員要像沙子一樣柔軟
很多演員在表演道路上都有階段性,不同時期對表演的認知都不一樣,但李乃文認真思考后,他覺得自己沒有所謂明確的階段或變化,哪怕有不同,也是取決于戲外人生的經歷不同,從一開始學表演,演員的目的就是接近最真實的,人物的反應。
至于怎樣才能真實?就拿最近這部戲劇舉例,《我們的日子》里,劉淑霞的母親得癌癥,李小冉沒有哭鬧,李乃文注意到不少彈幕說,劉淑霞這時候怎么不哭呢?是不是感情不真?
“其實這個認知可能會有一點偏頗,當我們全家人得知我父親生病的時候,每個人日子還是照常過日子,該治病治病,不會一下就哭得稀里嘩啦,不要認為沒有哭就不對,每個人的生活態度不一樣,包括劇里的姥姥去世,我和小冉說,我父親去世,我母親一滴眼淚都沒有掉,因為我在外地拍戲,當天我就趕回來,我就知道我不能在我母親面前哭,每個人心里都在隱忍,但是我看到我母親的一剎那,她的眼睛是干的,一點眼淚都沒有,但是我能看到她的眼神是空的。陪伴自己幾十年的老伴,相親相愛相依為命相濡以沫的愛人,突然離開自己的時候,心都是空的。什么時候哭的呢?后來她給我打電話說,兩年以后,她一個人在家的時候,突然就崩潰了。這個是真正的生活。我在現場也和小冉分享了這個真實的過程。”
他認為,如果沒有這個經歷,或許普通人都會覺得,面對家人得了重病,“應該”會是什么反應,這種“應該”其實沒有人教,而能夠演出無限接近真實的反應,只能來自自己經歷過,“演戲跟人生一樣,看書也好,經歷也好,都是點點滴滴積累的,潛移默化會影響到你,所以不同時候對于所塑造角色的這種深淺度可能也會有變化,每個人的經歷都不一樣,所以誰也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定真實與否。”因此生活本身對他而言,就是他做演員道路上的財富,“要看你怎么去悟了,我只是善于去利用經歷。”
這種利用,李乃文稱之為“自省”,“不僅是工作上的自省,是生活里時時刻刻全方面的自省,這對表演是有幫助的。”
至今他也在思考,對演員而言,應該走近角色還是把角色拉近?但他覺得,不管遠近,作為一個演員來講,首先要具備一個特性,就是要柔軟,“要善待每一個角色,把它當成是你的朋友,從很多方面去了解他,如果劇本沒有給到,就要腦補,不管是筆頭上還是腦子里去刻畫,要真真切切要能明白他了解他。或者說,要能換位思考,站在他的角度去看待戲中的一些人一些事,找到正確的人物關系。”
“演員要像沙子一樣。”有時候和同行討論演戲,雖然“到底什么是好的表演”這一課題沒有結論,但至少得先如同沙子般柔軟,“每個角色都是不同形狀的容器,沙子能在不同容器里變成不同形態。”
“他們不是專業的,但我們是”
但這種“變化”里有需要堅持不變的東西,比如在不同時代里,觀眾喜歡什么樣的演員都不太一樣,幾年前觀眾大夸特夸技術流,不久后好像又流行真實感,當下觀眾又喜歡摳細節,看人設。李乃文演了二十多年戲,不覺得演員需要因此去改變自己的專業判斷,本身根據不同導演不同劇組,都要做調整。
“演員喜歡的和觀眾要求的,不存在有矛盾,第一要看是什么樣的戲,第二面對的是什么樣的角色,每個戲本身就有不同的演法,要跟導演去溝通,看他要求你是自然的,還是有張力的,一個戲的風格要統一,整體是導演在把握,我是非常尊重導演的。一個戲出來以后,里面的方方面面是有‘呼吸’的,‘呼吸’要順暢,觀眾看著才舒服,所以說我認為,沒有什么角色我必須要怎么演的問題,我沒有一個特定的概念,要看呼吸的需求。”
如果觀眾真的有對演戲方法的喜好區別,他倒覺得,也應該由演員去引領,“文藝工作者自身是有責任的,要把好的東西帶給觀眾,在潛移默化里影響他們的審美,不能一味去迎合,不能一段時間流行什么就演什么,有些觀眾說喜歡特有張力的,你就去演那樣的,不能這樣,本來觀眾的口味就眾口難調了。演員得有一個對于自身職業的認知度,要知道你自己到底是誰。審美總會慢慢提高的,你得好的東西去帶觀眾,他們不是專業的,但我們是專業的,應該是我們去影響觀眾,而不是讓觀眾影響我們。”
這種責任感也包括挑選出足夠好的角色呈現給觀眾。李乃文挑劇本并不是隨便看看,是要費一番工夫的,“要看他身上的故事精不精彩。不光是面前的,還有他身后的故事。”他會對角色進行反推,通過劇本給到的人物,他的行為,反推他為什么會這樣做。有的角色可能眼下做的事有意思,但是推背后,這個人物推不動,那就沒什么意思了。“在我的字典里面,沒有純壞的人,總是有原因的。只有壞,沒有人性的另一面,這個人物就太單薄了。”
李乃文強調,演員到最后拼的是文化,是理解能力。怎么才能具備這些能力呢?“那就要多看書,多看片子,要增加自己的閱歷,最后才可能有能力去解讀一個人物。”在他拍戲如此“勞模”的情況下,依然保持觀影頻率,并且非常跟得上時代,采訪的當下他就推薦了電影《西線無戰事》,并且提及要回去補課電視劇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。
父母不同尋常的教育
李乃文在不同的采訪里都提到母親的影響。
母親是一名話劇演員,從小在耳濡目染下,李乃文萌生了做演員的心思。到了高中,他在市重點學校,雖然放在全市范圍,他數理化成績不錯,但放在自己班級里,是令班主任頭疼的存在,最終他決定報考中戲。
盡管從小就在臺上臺下看母親表演,但報考過程并不順利,當年他只能作為自費生進入中戲。某種程度上,這件事真正給李乃文帶來了人生上的大轉折。
那是經濟形勢并不好的時代,每家能拿出來的錢都很有限,公費生一年學費幾百塊,而自己家要一下子給出5000塊,這種壓力對父母而言有多大,相當于要借錢上學。李乃文忐忑不安,壓力很大,心里非常難過。母親找他談話,“她告訴我首先別有壓力,其次提一個要求,希望我上了這4年大學之后,讓老師認為讓我自費是錯的。”李乃文覺得母親非常智慧,“不會給我壓力,同時還給我動力,用她的方式讓我一下就輕松了,同時還有了一個目標。”
李乃文僅用一個學期,就實現了母親的要求,學期末的匯報演出,小組排戲,李乃文參加的小組都讓老師很滿意,并且在每個組他都是主力。老師當著他和母親的面,都表達了贊賞以及“后悔”。
這倒不是李乃文故意較勁的結果,實際上從他在中戲第一天上學開始,他就像一條魚回到海洋,那是在享受,不是在學習,在表演領域里的游刃有余,讓他絲毫沒因為“自費生”這個身份懷疑自己。
這種自信平和,不僅來自他的天賦,也和父母從小的教育息息相關。
“我小時候總搬家,那個時候一搬家就得轉學,我曾經轉到一所小學以后,班主任特別不喜歡我,不知道為什么,我在他的眼里就是特別不聽話。但是我父母知道以后不會覺得是我的錯,我轉過幾次小學,除了這個學校之外的老師都喜歡我。他們信任我,為了讓我不要自卑,一個學期以后他們就毅然決然讓我轉學了。”
這種信任給他的影響,遠遠大于母親在專業上給他的影響。同為文藝工作者,母親很少和他討論演技上的問題,更在意的是他的為人處世。
李乃文記憶猶深,剛開始演戲時,有人在路上認出他了,他當場很不好意思,一緊張就下意識躲開了。母親對此很不高興。李乃文疑惑,從小父母都教育他,為人要低調,這時候承認不是顯得很高調嗎?母親給了他另一種角度的答案。
“人家認出你來了,說明你演得還不錯,這是對你塑造角色的一種肯定。但你不承認,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好像把自己和其他人區別開來。但演員也就只是一個職業,跟老百姓其他職業只是分工不同,性質不同,但其他方面是一樣的,不承認就是你心里認為自己是特殊的。”
有段時間因為拍戲,李乃文和家里的聯系變少了,父親悄悄告訴他,快給母親打個電話,母親認為他這是“膨脹了,覺得自己忙到可以不管家人了”。
“演員也就只是一個職業”這個觀念也實實在在根植在李乃文心里,演戲這么多年,遇到大大小小的事,他對演戲的態度一直沒變,“他們讓我知道自己的職業認知到底應該是什么。不能膨脹,也不要過度自卑,心態擺好,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。”
李乃文覺得,表演這一行,本身更多是靠悟性,“師傅領進門,修行在個人,表演是屬于個人的,獨一無二。態度問題擺正了以后,剩下的路自己去走吧,他們是開放式的教育觀。”
大導演的人格魅力
最近兩年李乃文接連拍了張藝謀導演的《懸崖之上》《堅如磐石》,對張藝謀深感敬佩。
“因為疫情,我在山東有一個戲沒有拍完,要回去補拍,當時正在拍《懸崖之上》,我就跟他(張藝謀)說得請個假,他馬上說可以理解。但晚上要跟B組導演還有動作指導開個會,把時間安排溝通一下。當天我們拍到凌晨兩三點,第二天制片人跟我說,回去后張導連夜開會討論,第二天他告訴我可以請假三天。當天晚上我們又拍了一個大夜,張導團隊的人告訴我,從沒見過導演這樣,一遍遍拿對講機,親自在催時間。這個事讓我特別感動,因為他知道每個劇組都不容易,也知道演員在這個時候是最難的,不好意思再催時間,于是他自己主動催,情商特別高。他這么大名氣的導演,卻尊重每個人,能夠換位思考,設身處地知道你的難處,盡可能幫助你,這就是人格魅力。”
李乃文覺得每個合作過的導演都令他受益匪淺,尤其是在職業上持續多年不斷付出的心力,也讓他感慨。
“他們太愛自己的職業了,張藝謀、陳凱歌、馮小剛導演,你通過他們似乎不知疲倦能看得出來,一直保持高強度的精細工作。他們可以24小時一直在拍戲,每個鏡頭怎么弄,要跟每個演員說說表演,方方面面,他們在自己的領域里是不知道累的。平時我也會觀察,凱歌導演平時每天一大早第一個到,最晚一個走,演員有休息的時候,導演沒有休息的時候。張藝謀導演也是,時時刻刻都在現場盯著,回去以后還要開會,討論明天的劇本,還要去機房看粗剪,不滿意的話怎么去修改,你想他能有幾個小時睡眠?他已經70多歲了。這是他們的共性,我很佩服的一點,也在激勵著我。說白了做事情真的要有一個好的態度,沒有態度的話,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”(澎湃新聞記者 楊茜)
舉報郵箱:jubao@people.cn
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:010-65363263
由《環球人物》雜志社有限公司主管、主辦
Copyright ? 2015-2024 globalpeople.com.cn.
版權所有:環球人物網